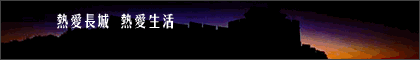|

|
 |  虎北口纪事 虎北口纪事
(六)睡在潮河畔
箭扣 2003年5月20日 发表于长城小站 |
 |
长城小站提醒旅行者和背包客:长城的存在,源于您我的爱护!
夜已深。我起身回屋歇息。
诺大个院子里黑漆漆一片,我摸索到自己的房门,进屋,开灯。灯光和从店家屋里倾泻出来的白炽光遥相呼应。
心里一时还平静不下去。相去不远的房间里住着刚才见过面的两个雇工,他们到底是干什么的?年轻一点的那个人的眼神为什么那么不友好?思来想去,也许是年纪相仿,但穿着、谈吐、经历的差异,或者是一个在游历景致,一个却要在为生计劳作,让他心难平衡?
我住的房间在院子深处,紧挨院后墙,墙外则是河滩地。最后检视一下门户安全,熄灭灯,我枕戈待旦。
公路上重型货车的碾压声渐渐平息,枕畔传来潮河水在石间穿流,潺潺作响,象是夜半歌声,温柔而舒缓。我在这轻软声息中渐渐放松,起了睡意。
半梦半醒之间,令公、七郎来了,北口的参将、都司来了,蒲松龄捧着他的《聊斋志异》来了,纪晓岚拿着他的《阅微草堂笔记》来了,冯玉祥将军骑着高头大马来了,关征麟将军率149团将士来了,大家服饰各异,长枪短棒,作揖的,拱手的,抱拳的,拥抱的,象是老友重逢。文臣武将,把酒临风,指点河山,我穿梭其间,引为忘年之交。客居异乡的夜晚我并不孤单。
突然,我被异响惊醒。手迅疾去摸枕下的藏刀。
声音来自房顶上纸糊的顶棚,悉悉嗦嗦。原来是小鼠在扮演梁上君子,从房顶的一角一趟趟出出溜溜到另一角,忙得很。
长舒口气,睡意又消。借着屋外远处被邻近场院的灯映得昏红的夜光,我看见自己呼出的热气在冰凉如水的夜影里飘荡。"山苍水白卧牛城,三尺黄旗万马鸣。半夜檀州春秋月,河山表里更分明。",在这样一个古老地方和静谧夜里,更更分明的还有借助自己吐纳的气息,我平生第一次清晰瞥见自己生命的步履,象眼前轻烟匆匆飞逝,象耳畔流水淙淙美丽。
明天,我要将这个生命之旅延伸去白马关。一路上,"山之南,地则五谷、百果、良材、美木无所不有",还有潮河川、南天门、香水峪、陈家峪、东西驼古岭,这些名字在未及动身的前夜就已经开始牵引着我,让我如此忐忑神往。
听啊,河声依旧。
千百年啦,有多少婴孩在它哼唱着的摇篮曲中熟睡,有多少男女在它荡漾起的河风中互传情谊,又有多少壮士此地一别而从此天各一方?昔时人已没,今日水尤寒,此刻,我在它的身边入眠,河水流淌进我的梦乡,也灌溉进我生命的河床。
今夜,睡在潮河畔。
(七)姊妹楼
姊妹楼,也叫双楼。我更接受姊妹楼这个叫法,有血有肉,让人牵挂、心疼。
自从上次听店掌柜提到她们,到如今,这个名字在我的心中已深藏多年了。我本以为她们将会永远这样虚幻地陪着我一直到地老天荒,可是有一天我却不经意看到了她们的留影,才印证了掌柜的话。
姊妹楼,她们两姊妹确曾活生生地在人世间存在过很久,并且也只是在不太久以前她们才羽化仙逝,真正离我而去的。现在想来,当天从卧虎山东端下城时的的确确感觉到四下空缺了些什么,象是不自然的嘎然而止,我当时还觉着蹊跷。
我认识一个经营理发店的小伙子,我常去他那儿理发。小伙子从小长在虎北口,据他讲那时虎北口可有得看了,姊妹楼是其中之一,还有遗存下来的和长城同属一体的过水门楼,还有城上分布很广的文字砖,上面修建者、督造者、点验者,姓甚名谁,大小官阶,一应俱全。童年,他和小伙伴们就是在城台、墙砖、庙宇、塔檐间长大,长城和围绕长城的故事给了他们无尽的快乐和哺育,而如今,这些都已所剩不多了。写到这儿,我想说,我惟独一直没有把令公庙单写一笔,因为那里现在保护尚好,知道和景仰的人也不算少,我知足了。
姊妹楼是我纪事里可以记录的最少的部分,因为她们现在只活在褪色的黑白相片里,只活在小老板们追溯的话语里,我就只能对照着她们的遗像,加上后人断续的旁白,去揣摩她们曾有的丰腴和美态。
也许有一天一早醒来,我发现我的记忆也已经经不住岁月消磨,那时,天才刚放亮,我也要辞别市侩庸碌,立刻出发,去追寻她们神秘和安详模样。
苍穹下,从早到晚,我不停地走,一路呼唤着,就象填海的精卫,嘴角沁出鲜血,还一遍一遍,一遍又一遍 … …
《虎北口纪事》,写着,想着,痴痴地思念着,窗外,忽然传来隐约的歌语。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
那歌声悠远、伤感而幽怨,一下一下,抽打在我的心坎儿上。
[ 返回专辑首页 ]
欢迎指正,欢迎投稿!!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