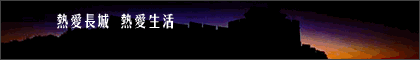|

|
 |  虎北口纪事 虎北口纪事
(三)长城
箭扣 2003年5月20日 发表于长城小站 |
 |
长城小站提醒旅行者和背包客:长城的存在,源于您我的爱护!
天刚蒙蒙亮,我从河东跨过大桥,踏上河西的土地。河西古称柳林营。
空气中飘着大雾,一路上人烟稀少。我完全是凭感觉来判断行进的方向。天色越发亮起来,我走进一座小村。
迎面遇到起早的大娘,我上前问路。"这天儿上边墙,路滑,加小心!"大娘的关心足以驱散我眼前的迷蒙。
拐上黑乎乎的煤渣路,走上一道大坡,已能远远看见右前方高高的山岭上浓雾漫卷,隐约显现长城的身形。我又没了目标。
听见不远处传来"辟辟剥剥"的砍伐声,我循声过去,见一位衣衫破旧的中年人正在劈倒一人多高的矮树和灌木。这里人还保留着烧柴的习惯。
中年人有些耳背,我最后贴近他的耳朵,近乎喊起来。
顺着他指的方向,刚想继续上路,身后却又响起砍柴人的声音:"你知道48年吗?4-8-年。"
"知道呀。" 我停下来,说。
"48年,上边打仗,死了好些人,这天儿一个人千万别上去啦!"中年人一脸认真地劝阻说。
望着山上的迷雾,神秘莫测,心里面还是略略犹豫,他这样好意,也一定有他的根据。不过,我盼这一天的到来已说不清有多久了,是不能够临阵退却的。
离开界线分明的大路,走入山中小径。盘旋而上,绕上另一道山脊,眼前就是举步可及的长城城体,坍塌得不及一人高矮。向下望,一条人工开凿的道路把从东面远处延伸至我脚下的这道山脊、并继续向西侧山冈上攀爬的长城拦腰截断。
我下到断城处,小心抚摩它的伤口。大智慧的人类挥刀斩下的地方紧邻一座碉楼,现在它的断骨曝露在空气中,望进去,曾经紧凑的内腔变得零落不堪。
基堞还在,长方条石宽大厚重,但已被蚀去表面,露出沉积在石块纹理内部的小贝壳。
"我来看你来啦,我的长城。"我一下变成个孩子,独自喃喃着,守在血流尽了、失去知觉的父亲身旁,一腔愧疚、安慰和挽留涌上心头。
从那里开始登城,山势并不险峻。脚下寸草泥土碎石被雾气浸湿,透着松软新鲜。缓缓前行,怕脚步放重了,会再增加父亲躯体的痛楚。
一个人越走离山下的人烟越远,离山顶高处的神雾就越近,不及近身,也已分明感受到它万千气象,不定变幻。穿行在湿漉漉的空气中,前无故人,后不见来者,只有妻的笑颜、大娘的嘱咐、柴夫的警言,在我身侧忽左忽右,时隐时现。我警觉地走着,我忽然联想到老国王常常在大雾弥漫的高台上向哈姆雷特讲述自己为奸人所害的细节,也许我今天所置身的迷雾里,也会再现柴夫所讲的那场鏖战中战死者在气息将尽的最后时刻血肉模糊的面容。
慢慢的,城体不再象我此前经过处那样败落,逐渐可以推见它原有的面目了。都说高处不胜寒,可长城在越高寒的地方反而幸存了下来,在低缓靠近人居处却只剩一垄,这又该责难谁去呢。
前面有一道极陡又高的阶梯,我心生快意。提步蹬爬上去,不容直立。背囊被阵风吹得直要后倾,如果不全身帖服在砖台上,不用手抓牢,稍不留神,一定会失去重心,仰面坠下。
翻过这道坎儿,我坐在梯道尽头的碉楼前。山势和视野在这里一下得到提升,放眼望去,脚下刚才一路行来的群山、城堞还如我初涉足时那样安详而静谧。山谷里铺设有火车道,一定常有火车从它身边呼啸而过,可它却一再告诉我说天底下断不再有什么可以让它悲喜交集的了,任凭石破天惊风吹草动、迎来送往冷暖亲疏,都不足以改变它和现在一样的表情和心境。多少年呀,目睹过太多的世事沧桑刀枪箭戟生死更迭,它完全有资格这样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它就算一言不发,也足以把震撼贮进每个到往的过客的血脉里。只要,他们还有一点血性。
时至晌午,太阳出来了,云消雾散。远方另一片山坡上,羊群漫漫,一个老汉蹲踞在巨石旁,悠然享受和风和暖日。正是羊儿贴秋膘的好时节。
距离制高点还有几座烽燧的间距。我站在另一座碉楼外,仰视楼顶。垛口已经荡然无存,惟有一条吐水石槽孤立地探出墙沿,凛然天外。
连石槽都风化了呀,棱角变得模糊,砂岩粒粒可辩。它坚持在原地有多少个年头啦?岁月多无情,枪炮多无情,锄镐多无情,淡忘多无情,那你究竟还能在那儿坚守多久呢。你也了解世间没有什么可以逃脱自然规律的收服,那你一贯的坚韧又为的什么呢?
一路走下去,我一路理不出个头绪。
下一座敌楼建在一处地势较前面低的地方,且坍陷严重,内部拱廊一眼望断了天。出于特殊地段考虑,在楼与城墙步道贯通的下首没有留下门洞,却在另一头墙下的关内一侧开了扇砖券拱门。出拱门,斜刺里一道山梁,长着一片苍松,我推想这里过去定是有路通往山下,或是城墙的西首。一旦战事吃紧,山下或者西端高处的援兵可以籍由此入口上城增援,上下呼应,将来犯之敌赶下城去。松林年头不会很久,直直地长在山梁插向拱门的小路旁,一开始,我从拱门内拐出来,视线猛一下暗下来,真以为眼前突然站出些人来,再看,密密麻麻的,里面或许可以设下一队伏兵,刀出鞘、箭上弦,杀气腾腾,令人胆寒。
不懈怠,不停步,再攀过一条临渊的长长梯坎,已然抵达最高峰。这里空间豁然开阔,长城在草丛间坍废成一道石砌矮墙辗转向前,直伸向一座外墙上伤痕累累的孤楼。
它是这段长城的最高境地,就是早晨从山下望到被翻滚的迷雾笼罩的所在。除去神秘面纱,我仍然敬畏它,趋向前去抚摩它一袭发黄的铁衣,上面坑坑点点,斑斑驳驳。抚触它的时候,我说:是什么伤得你这么深重?你只说给我听吧。它一声不响,让我看不透它所经历过怎样一场场洗礼。感觉,和那具被慢慢剥蚀的吐水石槽以及山下所有风餐露宿在荒野中的敌台城隘一样,它们秉执同一种信念,那就是宠辱无惊、生死两坦然。
没有什么比看到自己最最衷爱的人独自承受创痛却咬紧牙关默不作声更让我无地自容和痛彻心肺的了,可我还要追问为什么你明知有那么多无情的、或是暴风骤雨、或是积年累月的摧毁和销蚀,你还威武不屈、不跪不降、不退隐于我的眼眸?
我知道砍柴人提及的四几年的那场保卫战,一百多条鲜活的精壮生命在血与火的瞬间永远留在了这片山冈上。那时,你曾亲眼目睹,那么多人在危难时刻义无返顾地饮弹倒地,就在你身边不远,他们不作寻常床箦死,他们的热血浸渍在你的胸口,而你不屈的影子也映在他们逝去前永不瞑目的留恋的一瞥中。就是为了这些吗?我看得出你的不甘,我看得出你忍在眼窝中的热流,你和他们默默相许,永远为彼此焚香,为彼此守灵,纵使有一天灰飞湮灭,也要化作彼此坟头的一抔新土,长出嫩芽,焕发新绿。是这样吗?
不远处,倒卧着一具象是旗杆座的石构件,多半截埋没在泥土里。我想起八百里秦川和湿泥化为一体的兵俑,容貌生动,和它们相似,一听见我近身时的心跳,或是不小心弄出响动,这神物也会一骨碌翻身爬起来的。
我缓步登上楼子西南侧兀立着的一座山尖,我还想一直走下去,然而前路已被深涧阻断。隔谷相望,对面峻峭的峰岭上还有烽楼镇守,我的人儿已经无法踏足,但我的魂灵早已第一时间飞越沟壑,与它神会去了。
孤鹰在山间盘旋,忽而俯冲至悬崖边,忽而扶摇直上青天,那是长城和在此守卫者、殉国者的天葬,荣耀与梦想同在。
[ 返回专辑首页 ]
欢迎指正,欢迎投稿!!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