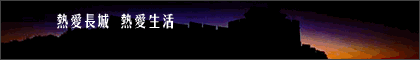|

|
 |  风雪长城路 风雪长城路
箭扣 2002年6月2日 发表于长城小站 |
 |
长城小站提醒旅行者和背包客:长城的存在,源于您我的爱护!
那段长城,伴着早春的乍暖还寒去过,顶着严夏的烈烈骄阳去过,披着深秋的天高云淡去过,惟有冬日里还不曾去细细端详它的模样,聆听它的言语,这似乎倒写就了我心中永远的传说。平日里的一片孤寂,一个遐想,甚至于一句梦呓,都会勾起我灵魂中关于它的传延,恍如冷冷流淌的气息里夹带着的发自遥远山地的神秘呼唤,回音绵绵,萦萦不绝,也引得我寻寻觅觅、依依难舍。
原定的跋涉没有料到竟然与元旦的一场大雪不约而同了,头一天飘飘扬扬了整夜的雪花儿象是为心底里期待许久的这次历程抛洒的华彩,那份清寒冰冷在熟睡的温暖香甜中悄然而至,却更让赶早醒来又将领受那场永久仪式的眼神里充盈着原以为只有一饮而进高粱烧酒再撞碎杯盏掷地有声才有的毅然决然。
同妻一道出发了,向着群山的方向,向着古老边墙的方向。
燕山积雪大如席,小时侯就曾听人说起过。如今,这方雪凌花儿一夜之间飘逸挥洒、巧妙编织的席子正浮出少年的梦幻,正宽厚直白地覆盖和包容着视野所及的一切生灵,山形的遒劲错落被拥堵成柔和服帖,树影的楚楚动人被包裹成冷若冰霜,就连平常热闹的日子也被封装成今儿个只有微风、只有枝头雪绒跌落、只有脚踏雪窝吱扭作响的宁静。从儿时延续至今的时光已经把早年的很多影音都磨褪了色,惟独这一句诗话带给一个年轻心灵的对一个方位并不很确切但肯定广袤苍劲的场景的无尽冥想却从来都挥之不去,印象深刻得直到今天长大成人真的踏上燕岭雪原,重又在记忆中寻获了它的下落,要印证一个不知和谁早就许下的约定。
远离村落,路就被雪掩映得失了踪影,不迫近它,就难以一眼辩识它的方向。幸好一溜土埂旁边,两座矮丘之间,几簇顶雪卧寒的枯草都能成为前路的目标,盯着它,踏足过去,就往往可以寻见下一步的所在。远处山岭的清亮背景代之以灰暗迷蒙,平日里或许一览无余的乡间土路走着走着也更见迷离,不知它会在身前突然拐向何处,只有绷紧眼力,毫不松懈地跟定彳亍,任它带去山神的脚下。
一大一小两串脚印擦过雪白勾勒的曲线,亦步亦趋,雪路也已经开始向下延伸,它要穿过一道深沟,爬上对面的山梁了。厚雪深埋谷底,仍隐约可见往日溪水繁盛时冲刷的轮廓,然而,曾经在这流淌过的水生命此时却不知漂在何方,是被谁倏地收了去?也未可知。眼前坡地上长着几株笔直的朝天杨,无风的雪后它们裹着冬衣,静静地立在那儿默默相对,不愿张显,只为相互间这一生一世永恒的守侯。下了坡,一大一小两块圆石,紧挨着,顶面包满了积雪。走近它们,大的稳重宽厚,小的眉目稚嫩,伸手过去,竟有温感,那份憨态可拘呦,象是被妈妈厚实的羽毛体贴护佑的鸡雏,酣睡中蹭个痒,好困,好暖啊。别惊扰它们,妻怜爱地说。
梁坡上开出了田垄,凭直觉,寻着田埂堆筑的小道,向雪雾弥漫的城垛进发。
又飘雪了?不是。怎么雪粒打在脸上?原来人儿已经站在山梁的鞍部。山风横扫过低凹的豁口,卷起雪尘扑面而来。雪是新鲜的,飞舞的空气是新鲜的,才发现妻冻得漫溢脸庞的红润也是新鲜的。
为妻整了整额头有些凌乱的发梢,接下来的羊肠小路看起来似是而非,盘绕在光溜溜的石坡上,不知所向。坡度之陡斜,轻盈的雪飘落下来,立足未稳,便不时被伏地疾行的风扬起旋涡,掀到半空,再抛下去,滑落山崖。于是,这儿的雪薄薄的,难以持久;足迹淡淡的,转眼不见。莽莽山野,行来两个传奇中的踏雪无痕。
只有风动,只有雪鸣,只有山影,只有空旷。两个人不时关照着,鼓励着,笑对着,一步一个脚印,却难以平息彼此眼神里间或闪过的、对谁也说不清无垠的荒原雪岭中将会有怎样一番等待的那种迷惑和期待。真以为就要这样一直走下去了,然而,盘过刚才的石径,不会想到,一座野村竟然就在没有人声,没有犬吠,没有鸡啼,没有炊烟,没有一丝一毫存活的先兆之下撞进不速的视野,悄无声息,也回避不及。它就隐没在皑皑白雪里,隐没在皑皑白雪覆盖的狭窄山坳里,悠然而独处,清幽而安逸。不见穿梭,不见寒暄,只有屋檐下干红的辣椒,窗台上焦黄的倭瓜,院落里晾晒的布衣,门脸上红艳的福对儿,静静地,一扫而光一路行来眼界里的苍白和单调,冷酷和悲凉,活生生地告白着严寒中一个群落的存在与鲜活。不管是否陌生,是否注视,是否关爱,是否怠慢,是否嘈杂,是否平淡,又是否关山阻隔寂寥无声,生命都要如此坚韧吗?和干道边随处可见的村庄截然不同,在歧路荒僻,难寻人迹,翻越雪岭后不期而遇生机的隐秘脉息,再没有如此情境的遭遇能让心底翻涌感动,让眼里汪满热泪了。怔怔地呆在坡顶望了许久,任凭寒风撕打在脸上,倒灌入脖颈。
仅仅几分钟就可以穿越的山村,一切仍在沉睡。经过山民们的小院时,期待着院门被吱呀一声打开,然后探出孩童的碎花袄裤,一串嬉笑,一串顽皮,或是偶遇夜短起早的老人,慈眉善目,冲着你憨厚地说:“二位打哪儿来呀?”……
什么都没发生,甚至先于我们而留下的足印。大雪湮没了荆棘的尖刻,少了阻绊,少了割挂,踢开草枝缀满的雪桃,丝丝凉意蹿入鞋袜裤管也由它去吧,一气儿走上村后的高坡,一气儿冲上龙泉峪梁尖儿上的敌台,两鬓挂满汗水结聚的冰棱,一下儿扑倒在城头的雪窝里,回应着心谷中那个猎猎扬扬延绵不绝的召唤。
抚摩着,徘徊着,凝立着,冰冷的城垣愈见严疆绝塞的彻骨;轻扣砖石,微顿双足,空荡荡的回声里都能听得到振武营右的虎虎操演。跪在雪中,贴扶着垛墙的时候,没注意,妻已转入了一座栈楼。随后而入,暖了许多。凑近窗洞,本想远眺一下,找寻哪怕一星半点儿的人烟,反又领教了山风的劲道。只是这里并非四下兜头而来,诺大的气流在涌入狭小窗口、残缝的一刹那被阻挡、分割、压挤成缕缕束束,吹进来,不大不小,不狂不卑,乖舛了许多。就在这降伏的风气里恍惚送来一高一低听似出自老远处的吆喝,时急时缓,再屏气侧耳,似乎还夹杂有犬的狂吠。该是一老一少爷孙俩吗?牵着爱犬?荒山雪岭,他们在做什么?忽然想起半山腰雪地上倒见过野兔游走觅食的蹄迹,哦,原来野山自有其博大,瑞雪自有其恩典,雪屋中,一团跃动的干柴炭火,一壶温热的陈年老酒,一锅肥美的野味山珍,一件祖辈的迁徙故事,就足以驱散隆冬的苦寒、深夜的清冷和生命的无助了。琢磨着,这声音越来越近,越听越清晰,心中顿生欣喜,仿佛已瞧见孙儿稚气未脱而余兴未消的脸庞和长者腰间倒悬的山鸡长着斑斓的翎翅。起初这声音真的是越来越近,然而,它却又一下子消失得再也捕捉不到它的些许音讯,消失得就象阳光下沙地上的残雪,一阵轻烟儿,踪影全无。祖孙俩儿终究没能走进两对儿企盼的视线,也许它终究是要越走越远的。
时间还不算晚,天却忽然更加暗下来。奔出容身的楼台,一股升腾的雪屑劈头盖脸撒下来,凉出个寒战,但见西北风从塞外浩浩荡荡扑天而至,它撞向山北坡,分成几路,顺势而上,把一路网罗的雪尘推拥至山顶,再反卷抖开,抛洒成弥漫的雪雾,阴霾徐徐不散。雪幕为旗,草棵作箭,千百年来它就这样无数次地进进退退,无数次地呼啸呐喊,无数次地攻打着耸立在它前路的敌人,只是面前岿然不动的山和山顶上巍然屹立的墙也无数次地抗击着这无休无止的冲锋,也始终没让风鼓动的大军越雷池半步,所以来路上才有山坳里安详的子民,才有屋脊顶无惊的卧雪,才有经年的窗纸,才有不灭的炕火。
天真的要暗下来了,山顶上走下一高一矮两个相扶的身影,雪又下起来,将这两个身影描绘成朦胧。再次途经那座安享孤单的无名小村,它竟还是一如初遇时的宁静。转过村口 老树掩映的院门时,眼前一晃,依稀认出一张手帕大小的粉红薄纸,上端贴在门楣上,下端剪散成穗儿,悉悉娑娑,在风中张扬。妻说,这里人把它唤作“挂钱儿”。数九寒荒里很动听很富贵很祥瑞的一个名字。一路走下去,心里老放不下这个山村院门口上直到离去的最后一刻才注意到的那个随风飘动的物件,是不是也可以叫它“挂牵”呢?慈母身在寒舍,眼眸却已久久地落在门口,落在风雪交加的石径,落在望穿了的山背后,一行清泪的光泽里映着游子的背影,或者,有点儿象电影《幸福的黄手帕》里忠贞贤良的妻子挂在枝头、迎接远行归来的丈夫的黄手帕哩。
雪越发大起来,白了黑发,白了衣衫,走出很远,还要回身投下留恋的一瞥,山脉、城隘、小村、野径早已模糊一片。总在想,寒夜降临,冷月之下,鹅毛飞雪,那里又该是怎样的一番景致呢?是“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的拼杀前的死寂,还是“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的殷殷挂牵呢。
眼前又浮现出那未曾谋面的祖孙俩,呼喊着,风雪中深一脚浅一脚追逐着猎物,忠厚的黄狗儿在身旁雪窝里不住地跳跃。这越看越象我儿时不止一次幻想过、又在年长后失落一方的城邦。
多年以后,雪地里,还会有两个红色身影,手牵着手,口里呼着热气儿,跳转着圆圈儿,我和妻,象两个沉湎于戏耍的顽童,一时忘了凛冽,忘了归途……
[ 返回专辑首页 ]
欢迎指正,欢迎投稿!!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