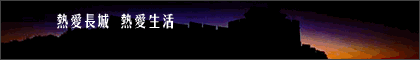"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提起丁玲这部名作,是在我们正驶上一条阳光照耀下的冰河,河道不宽,冰层却很厚,老李仍不放心,下车小心地走在前面引路。据他讲,这条河就是桑干河的一部分,当年丁玲的作品客观地反映了当地农村土地改革和农民的生活状态,老李说他也准备写一部"桑干河",讲述今日的农村,会触及许多现实问题,现在农民的生活太苦了……
穿过冰河,穿过满眼黄土墙的村庄,穿过蹲在墙根晒太阳的老爷儿们安详的目光。
每过村子,能见到的多是老人,常见的是废弃的房舍,残墙断壁间偶露精美的砖雕,无声地映现着昔日的兴盛和现实的贫瘠。
墩台连绵的土夯长城终于出现在眼前,镇川口到了。
昨天分手前,记者二牛专门跑回报社取来他的个人摄影画册《大同长城》,很郑重地写了题赠,送我们每人一本。画册中许多作品用光之精妙、构思之独特令人赞叹,看得出他对这一题材下了很大功夫,想不到这个两天来始终风风火火乍乍乎乎的大个儿,竟有这么细腻的用心。而画册中印象最深的就是眼前这一线长城。
爬上镇川口西侧的山顶,在120倍的摄像变焦镜中,密集的墩台重重叠叠,蔚为壮观。激动、疲惫、心巨跳,画面晃抖得厉害,忍了再忍,还是不敢按下录像键,放下摄像机,象牛一样狂喘。怪了,这山看着没多高,爬司马台也没累成过这样,是海拔问题还是老不爬山,怂了?!
下面半山腰上全顺儿和两位老李已经就位开拍,身后翟也不见了踪影,想必又寻了更好的角度去了,想去追他却一点力气也没有,索性就地坐下,支起相机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按几张过瘾。变焦头推推拉拉,连拍了十几张,身上缓过劲来,又开始满山遍野挪位置找角度,羽绒服、脚架、摄影包扔得东一个西一个。
长城延伸到山脚下,从北侧顺山势一路上来,快到顶处拐弯向后面更高的山顶攀去,这一段城墙异常高大陡峭却土质松软,似乎未做夯实,只借山体简单削筑而成。觉得上面角度不错,爬上一半方感觉没着没落十分困难,舍不得放弃,看看下面十几米的沟里雪很深,索性硬着头皮往上爬,大不了一头下去扎雪里。
分两次把器材运上墙头,腿已经有些哆嗦,倒着气儿,掏出摄像机把上来的路线扫一遍,真够险的,刚才要是有个同伴儿把自己爬的熊样录下来多好!镜头里真出现一头熊,是全顺儿正低着头在下面遛跶。一叫他,还真往上来。
"不成啦,过来接一把呗!"没爬几步,他便坚持不住了,上不来下不去地趴在那儿叫唤。我乐了,丢下机器蹭过去接他。
一起支好相机刚拍两张,身后传来翟的呼喊,原来领导已攀上了远处最高的山顶,而我们竟然正在他的取景画面中,要我们躲避,我的天!
得!成全领导!两个人又重新把器材搬下墙头,踩着松滑的泥土,地头弯腰贴着墙撅着,直到领导喊行了,才敢探出头。
蓝天白云下,翟扛着脚架在山顶大步行进,瘦小的身影意气风发。我急忙打开摄像机镜头,一边跟着他一边解说:"这是翟,刚拍到了好片子,正得雄赳赳气昂昂地往回走,而我们……"
"我们……我们在单位就受领导的气,啊……出来……还得听领导的,他得意了……瞧我们……都快成蒸熟的包子啦!"全顺在一旁气喘吁吁地笑骂着,满头大汗地又爬上了墙头。 我终于忍不住了,笑得镜头晃上了天。
李大光不愧是军人出身,我们的"2020"在迷宫样的沟壑间穿行,哪里转弯,哪里爬坡,他始终把握十足,对道路和方向简直是了如指掌。据他自己讲,这一带他每年都要来不下三、四十趟,如果十天半月不来心里就象缺点什么。为找到不同季节的最佳拍摄点,他专门用部队的军用地图研究过地形,而至今多少次坐骑陷进泥沼和雪坑他已经记不清了。
在李大光的指挥下,"2020"辗转攀爬,土夯长城时左时右在车窗外闪现,我来回摇着摄像镜头,口中念念有词:"现在是2002年1月4日下午,我们正在山西与内蒙交界地带来回穿插。"
"现在,如果正好在一个两省网络的中间点打手机,可以免费。"身边文化馆老李慢悠悠地调侃。
"可能吗?"我问。
全顺儿装着一脸认真:"嗨!说不定。"
翟扶着方向盘一乐:"嘿嘿!说不定收你双份通话费。"
车里笑成一片。
到达元墩,太阳已经西斜。这里的确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拍摄点,向西向东两个方向白雪皑皑的田野上,延绵伸展的土夯长城,联结无数座墩台高低起伏。这一带长城与北京周边长城的踞奇扼险、辗转盘旋完全不同,全部修筑在开阔平坦地带,并近乎直线构筑,而由于历史上属蒙汉交界的重要防御地带,战事频繁,几毁几建,形成了城墙高厚、墩台密集,城外有墩,堡营遍布的特点。
我们选择一处最大的带有外挡墙残迹的墩台作为拍摄点,正在选角度,下面又上来一银灰色桑塔那,下来几个背相机的,一见面与大同的两位老李都很熟,原来是同样爱好摄影的当地广播电台台长利用假日带着部下出来采风。大同摄影界对长城题材的如此热衷,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落日似乎总是比日出来得要快,雪野上黄土裸露的城墙和连串的墩台随着夕阳渐渐映红,画面十分生动。紧张地支机器,取景构图。从到大同手指就开始裂口子,越裂越深,一触冰凉的金属就钻心的疼,带着手套又碍事,索性摘了,十个指头已是血淋淋,弄得脚架、相机上血迹斑斑,顾不上了,只是连续按动着快门,今天要出好片儿了!
咋回事?取景框中黄金分割点上有亮点?抬头细看,天呐!是那电台台长的车,正停在七、八公里外的墩台下,车身在夕阳下闪闪发光。刚刚他们还在一起,什么时候跑了那么远!这片子拍出来岂不"穿帮"!
"大光,能跟他们联系吗?"翟在一旁焦急地问。
"我有台长的手机。"李大光肩膀夹着手机,手里小本子紧翻。
"他手机没开,我这儿还有他的呼机号。"李大光的语气愈发紧张。
眼看着落日已到地平线,长城墩台的红色在渐渐暗淡,我是又急又恼,扛着机器上蹿下跳试着挪机位换角度,但选好的构图都很难避开那刺眼的亮点,完啦完啦!今儿这好机会算瞎了。
"请急呼三遍××××,请把车向南开离长城二百米"。李大光一字一顿地重复了两遍。
焦心的等待中,那桑塔那终于缓缓启动,驶离了长城……
我们在夜色中进入了长城乡,"2020"晃着大灯,引擎声打破了村中的宁静,引得全村狗叫四起。卸下装备,房东已迎出来,我打开摄像机,从院门外一路拍进去。
院子不大,只三间北房,陈旧、拥挤却很整洁,正房靠墙摆着两台老式工业用缝纫机,东屋里一铺土炕占了半间,墙上贴着卷边发黄的《耶稣牧羊》和《最后的晚餐》油画印刷品,信教的房东老陈蹲在炕前给炉子生火,两位老李大声和他拉着家常,镜头中冒出一张天真的小脸儿,是老陈的小孙子。
老陈五十多岁,做过村里的文书,算是村里的文化人,老伴干裁缝,因为会做西服,在周围一带挺有名。一儿一女都已成家,儿子负责看护家门前一座移动通讯信号塔,每月三百元工资是家里最大的收入,却常常欠发。
老陈自家腌的咸菜、热乎乎的棒面粥和攸面卷,这顿晚饭很香,一天的寒冷和疲乏解了一半。吃饱喝足,脱鞋上炕烤丫子,雪里趟泥里踩一天,脚早已湿透冰凉,此时一炉旺火烤着,温暖幸福全身。
都没有睡意,聊,聊对摄影的见解,聊各自的经历,聊生活的真谛……
文化馆老李,至今留在大同的北京插队知青,无论生活的艰难波折,始终不放弃对艺术的追求,活得坦荡洒脱。
李大光,大同军区宣传部正团职转业,本可回到父母身边谋得更好待遇,因为不舍相识多年的战友和朋友们,不舍为之奉献青春的一方土地,毅然留在大同,而拿到转业费的第一件事就是买回一套乘心的相机。
全顺儿,到哪儿都能让人开心的活宝,处处照顾别人的大哥。
翟,我的摄影引路人和最信服的榜样。
这新年的节日夜里,在这远离都市的偏僻乡村的农家炕头,四位人到中年的兄长,真诚、执着、平静地谈论事业,讲述浓缩的人生,我由衷地体会到--感动!!
欢迎指正,欢迎投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