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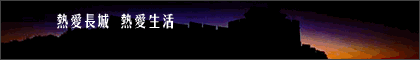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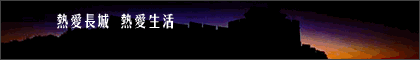 |
|
| |
|
狄仁杰 2000年10月16日发表于长城论坛 山西长城六日记之一:老营 十月一日凌晨的山西原平,天下着蒙蒙细雨。 昨晚我们从北京出发,开始了这次山西长城之行。十六个人精神抖擞,小范、爱晨、吉普赛和亦尘的妻、子前来送站。我在北京站前广场第一次看见了身着新式警服的铁路公安,还有全副武装,随时待命的铁路特警。车厢里拥挤闷热,我们巧遇回太原探亲的同路,他说多年来还从未见过去山西的车上有这么多人。在原平下车后,列车好象一下就空了一半。我第一个走出出站口,一盏大灯晃得我睁不开眼,原来是先于昨日到达的老陈在打信号,老杨在他旁边。 一行人跟着陈杨来到车站一侧的鸿宾楼饭店,老杨的夫人江月在此等候。早餐有葱花饼、烂腌菜、煮鸡蛋、馄饨和小米粥,当然更少不了醋。一下车就有这么好的享受,让歇了“沉浸在幸福之中”,不禁感叹:“这一倒醋啊,一碗平淡无奇的馄饨……”,亦尘接道:“就变成一碗醋了。” 据说,连下几天的雨,让这里的路变得特别地烂。果然,我们坐上中巴之后,所见路况真是惨不忍睹。好在这只是车站周边的一段,进了县城就摆脱了泥泞。我坐在车门旁边,风衣在包里,而背包又都被捆在车顶上取之不便,晓月就把他的冲锋衣给了我。 出县城,驶过两旁皆是农田的公路,渐渐进入山区。雨已在不知不觉中停了下来,远处的山顶云雾缭绕。此刻的我,真希望快旅太行穿越的队伍忽然从这大山的某个地方钻将出来,出现在我的面前。 朔州的汽车站和火车站相去不远,并且好象修得比火车站还要气派。我们在这里换车,十九个人被硬塞进去偏关方向的中巴,车里已经挤得几乎没有立锥之地,可贪心的售票员沿途还要不断地拉人。我坐在个空油桶上,被压得几乎直不起腰,羚羊的腿肚子转了筋。经平鲁,因修路禁行而需绕道,结果又经历一段更难通过的烂泥塘。乘客们纷纷下车步行,象黄花鱼一样溜着边过去,再上车的时候,好象又多了几位,连车顶上都有人。据说,在这里这根本不算超载!忍耐毕竟是有限度的,当售票员再次企图拉客时,乘客们终于提出了抗议:“别上了!”。 近三个小时车程到老营。下车的地方,北面是个道班,南边就是老营土堡。我们在众目睽睽之下背着大包走进城堡,看见堡内挖墙而建和砖石盖成的窑洞。堡中有古老残破的民居,不时可以看到几尊雕刻精美的石门墩。村屋错落,穿行其间不知怎么就进了人家的院子。堡子的东、西、南三座门洞还在,门额石匾均已不存。瓮城也被扒开口子做通道,城内种着玉米,城墙下堆满了秫秸杆。城墙上烟囱林立,有的是砖石砌就,有的干脆就是一口没底儿的破水缸。有的地方又种上了低矮的树木,我抓着带刺的树枝,从墙边仅容一足的地方小心翼翼地过去。淘气的娃儿们在我眼皮底下跑到别人地里偷东西,我视而不见。按村民的指点,我摸进小院去找他所说的匾额,却被院里一声狗叫吓得抱头鼠窜。 堡中有条东西向的主干道,两旁商号旅店林立。我们在看上去是此间档次最高的一家小饭馆吃了在山西的第一顿面条,然后又背包上肩,鱼贯而出,越过公路,沿小路向北上山。 北山上有座坍毁成马鞍型的黄土墩台,残存有砖石基座。据当地老乡说,这墩台是“文革”期间被来串联的红卫兵小将们拆毁的。村里还曾有一口明代古钟,敲起来声闻四十里,可惜在“文革”中也难逃厄运。当地人称长城为边墙,我们沿墩台下的边墙西行,见其北侧还有一道边墙,两者相距大约十来米,当中是一道深约十米的壕沟。这道边墙在山下是看不见的,它和南面的边墙平行,向西约一二百米后再转头向北。南面的边墙则是转而向西,距转折处约二十来米的地方又有一座墩台。登墩台四顾,老营堡全貌尽收眼底。远近山峰上,墩台一个接着一个,以西北方向最为密集。 当晚我们就宿在边墙脚下一片收获过的农田里,八顶帐篷分两行排开。晚餐时,火箭放起“二踢脚”,要庆祝晓月和小方结婚七周年。大家起哄,要他俩喝交杯酒,据说“五一”时这节目的主角,是累了和歇了。 山西长城六日记之二:晋蒙交界的边墙 早起,发现帐篷结露很重。先起的人们在外面大声说笑,害得我回笼觉睡不踏实。晓月带了三脚架,却忘了带相机,结果在山西的几个晚上,三脚架只落得用来挂营灯,他也拒绝谈论任何关于相机的事,而大胆小方昨晚却被黑地里一双黄眼睛吓得不敢单独方便(据说是只狐狸,未经考证)。不停煮的粥,让我想起了昨天在老营看见村民用大铁锅熬的那些热乎乎的东西。好汉对我这么外行很不屑:“这可是地道的燕麦。”有人提议,大家出学费,让小站杰出女性之一不停去考个厨师本儿。不知是谁把一盒没吃的鸡蛋给当了垃圾,结果在火上一烧,鸡蛋就接二连三地往下掉,令江湖大发感慨:就是鸡下蛋也没这么快呀。 收拾完毕,我们继续沿边墙前进。先是贴边墙一侧行走,一二百米后又转而走上拖拉机轧出的路。边墙缘山而建,走向多有起伏转折,大致是向西北延伸,于途多次被道路截断。离营地一两里的地方有个小山村,道路从村东低地经过。村中窑洞,皆依山而建,面向东方,俯视公路。长城则越过村西山顶,好似这村子的一道后墙。沿途的边墙,多数仅剩黄土,偶尔可见塌落处露出地基岩石,有的地方还残存有条石路面,有的地方,长城则只是一道土垄。道路在边墙两侧或东或西,有时无意中看一眼脚下,竟发现这里就是长城。原来长城既是道路,道路既是长城,你只晓埋头走路,却不知已经走上了长城。老王放声唱起京剧过门,我倒希望他来段山西梆子。 在营地看去离我们还很遥远的墩台,因我们不停的脚步而越来越近。墩台上小下大,有圆有方。保存好些的,四周还有一圈围墙,形成一个个圆形的小院。墩台的一侧,可以看出螺旋上升的阶梯痕迹。古时守卫边关的将士,就是从这里登上墩台,去观察敌情,点燃烽火。山间劳作的农民停下手中的农活,好奇地看着我们从长城上走过。可能对他们来说,这样背包走长城的人很不可思议。可那翱翔于长空的雄鹰呢,也许它只看见了一群蚂蚁。 行进间,可以看见山谷中有大片的窑洞,显然是个村落。小歇时,和一位老农攀谈,得知那里叫史家台。听不大懂老农那浓重的山西口音,似乎他在说东北方向一片有绿荫的平坦的山梁下面,有个阴窝沟。翻过那道梁,就是内蒙。大约是在西南方的山里,当年八路曾在那里和鬼子打仗。这一带有不止一处石砌边墙,其中有的石块大而规则,显然是经过了人工打磨。长城并不都建在山顶,有许多是在山腰之上。我和那老农开玩笑,说要这样一直走到辽东秦长城的尽头。羚羊的德国产登山鞋不大合适,磨破了脚后跟,午饭时他撕了安分带来的纸内裤来垫脚。小方纳闷:这是什么癖好? 午饭后沿公路继续走,我和好汉、大灰狼、江湖,还有老王等几个人在前队。在一个转弯处发现,如果沿着公路走下去会很绕远,而从这里下山谷,再爬上对面的山坡,就可能少走许多路。好汉先下去探过一段,回来说可以走,我和大灰狼、江湖未加多想,就义无返顾地一头扎了下去。穿过几片小树林,起初还算轻松,可越走就越觉得不对劲:前方树林越来越密,形成一张致密而多刺的网,或者说就是绞肉机。不但我们这样背着大包钻不过去,就算是硬钻过去,也得变成一堆杂碎。不能再走了,我们一边大声招呼后面的人不要再下来,一边回头奋力拨开拦路的荆棘往上走。等气喘吁吁地爬上公路,前队已经成了后队。这一下一上耽误了将近一个小时,还得说老王聪明,没跟着我们瞎跑。 老老实实走公路吧,还是这样保险。路上一片片的树林把长城隐蔽于浓荫之中,公路从林间穿过,两旁的小叶杨,叶片金黄,形成一条美丽的金色走廊。人行其间,心旷神怡。老陈在路边摘些沙棘,桔黄色的果子,看着就象花咕嘟,咬一口就是一股酸甜的味道。谁能想到,在几乎是满目荒凉的黄土大山深处,还有这样的世外桃源。 接下去又要闹笑话了。行进间我们这十九个人的队伍拉得很长,有时我就是一个人在走。一次在接近柏羊岭的地方休息时,我看见隔着一道深沟的对面山腰上有个人在向我挥手。看他虽不象我们队伍里的人,可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也对他友好地挥了挥手。可那人挥起手来却没完没了,并且他挥手的姿势,好象非人所能及。我走向前仔细一看,差点气歪了鼻子:哪儿是什么人,原来是头驴!那不断摇着的,是驴的尾巴!天知道,我的双眼视力可一直保持1.5。 柏羊岭距老营二十五里,有三户人家,二十来人,据说都是从别处临时来种地的。地是早就开出来的,现在政府不让开荒了,将来都要退耕还林。吃水靠天,也就是挖洞存雨水,不够了就下沟到离此七里的地方去打水。村民说,我们是中国人好说话,曾有外国人来这里,长得不好,娃子怕,晚上不敢让他们住家里,他们就开口骂人。村民听不懂洋话,我问他们怎么知道外国人在骂人,村民说从口气里听出来的,带着外国人来的是个北京人。这山上有时候有狼,离此三里远有个炮楼,叫“九窑十八洞”,当年八路在那里和日本人打过仗。现在楼被拆了,是口外的人来拆的。 北距柏杨岭不超过一公里的山坡上,有座方形的城堡,依山势北高南低。长城和方城平行至山顶,又翻过山梁向北下去。公路则向东北截断长城,再从远处一个山口过去。走到那个山口,发现这里也有一道长城,大致从东而来,至山顶和南来的长城垂直交汇。忽然间似有所悟,连忙展开地图,原来我真的站到了内外长城的会合处! 沿路向北,十几分钟后到达一座四眼楼,这是此行所见第一座,也是唯一一座保存基本完整的敌楼。外包砖、箭窗、垛口、内部回廊中厅大部分都在,外观颇雄伟,只有西墙不存。北京周边的长城里,这样的楼子并不稀少,可在这地方却是凤毛麟角,难得一见。这就是“九窑十八洞”了,并不如想象的那么残破。这楼子南面的四个箭窗很有意思,两个塌了上缘,两个没了下沿,远远看去,好象上下错了位,让我很是琢磨了一番。 途经野羊洼,我们想在此补充用水。可从储水池里打出的,是发了臭的雨水。山区缺水,这样的储水池随处可见。村姑说这水是喂牲口的,人喝了会闹肚子。看样子,她是不愿意让我们用她家的水。我们能理解,那可是人家的活命水。 时近黄昏,我们走到晋蒙交界的长城下面。经问路得知,此地离老营十五公里,最近的取水点是内蒙的水草沟,离此两公里,需要北行翻越长城,而下一个目的地水泉则还有二十华里。取水后,还要回头上山,沿长城西行。安分见天色已晚,建议先到水泉附近宿营,用光所有的水,明日早起再派人去打水,结果建议被采纳。大家离开公路,上行翻过边墙,在山梁上拍下天边一轮落日。长城在这里又有一个分支,北行斜下深入山谷。在山间择地扎营,为节水不煮方便面,只煮些菜汤,就着汤吃干粮。汤少狼多,歇了说小方该拿耳挖勺来分汤才对。火箭要连夜去水泉取水,但前方情况不明,安全没有保障,结果被大家坚决劝止。 饭后我登上长城,只觉一阵寒风扑面而来,原来是长城为我们挡住了西来的风。今晚的营地,似乎已经在口外。此刻的大都市,该是一片流光溢彩,可在那里,还能看见星星吗? 山西长城六日记之三:水泉 夜来有风雨。起身后,发现营地东面的山谷里还有边墙和墩台,和营地旁边的这道边墙大致都象东北方向延伸。有的地方,长城和山间的梯田已难以区分。八个人组成小分队,带着一大堆瓶瓶罐罐,越长城到三里外的水草沟去打水。 一路下行,耳闻晨鸡啼鸣。水草沟是个大村子,窑洞依山势高低错落,可见有老农在山腰间扬场。机井在东山坡上,用一根长长的白塑料管引至山下平地,有人在上面控制着开关。我们灌足了水,漏出的水流进下面的蓄水池。水草沟的居民是幸运的,能用上这么清凉甘甜,喝了肚子不疼的水。这里属内蒙清水河县辖区,因为口音相近,使得老家在大同的歇了能以一口流利的方言和村民交谈。我也在努力学说山西话,可总也学不好那一腔鼻音。村民说,从这里沿着沟走可到达水泉,一路上有村有水,沿长城线走就要绕远,并且没有水。可我们此来,不就是要走长城么。 离开水泉时,见农家院中升起袅袅的炊烟,村口也有漂亮的小叶杨。晓月说,村里没有狗。细听听,这长城脚下的山村好象还真的不闻犬吠。可古时候,这里也许曾经金戈铁马,不知有过多少血腥的厮杀。 回到营地,用罢早餐,收拾好营具,该出发了。小方陶醉于黄土高原的美景,不禁唱起“人说山西好地方”,又伸出她的胖手,“左手一指”,右手一划的,引来周围一片声的喝彩,也没人计较她唱错了词。江湖有事,要顺着水草沟这条路出去搭车,回内蒙老家了。临行前,大家纷纷和他道别,我站在山坡上,向他高声喊着再见。 原路向上,翻过长城,又回到山西境内。沿着与长城平行的公路向西走,上一个缓坡,坡顶处长城向北拐过一段,又向西而去。这一路的墩台、敌楼密集,好似涞源杜家台。小方在后面又唱上了,还有晓月应和,妇唱夫随,为小站晋军一乐。 长城在距营地有一小时路程的地方和公路分开,公路向西南,长城向东北而去。路口的土地上,有前队留下的路标。我又成了独行客,前后都不见人。沿途的长城,城砖散落,有的地方残存有条石墙基和青砖路面。远处不时传来隆隆的炮声,那大概是开山炮。山间梯田,摆放着成捆收割后的庄稼。山坡上可以越来越多地看见用刷了白灰的石头围起的土台,那是要植树造林。我寻着前队留下的脚印,或走长城,或行小路,最后下坡上了公路。山顶延伸下来的长城又被公路截断,并大致分作东西两路,西路在山脊上兜个大圈子又伸向东北,东路则向北一头扎下山谷。我沿着与西路长城平行的公路走,好汉从山顶长城上下来超过了我,说他刚才走过的那段长城保存得非常好,都是青砖墁地(后来晓月说,那简直是故宫太和殿)。回头看,山坡上用白石垒成个巨大的“水”字。 半个小时后我和好汉越过长城赶上了前队,见到自称要“笨鸟先飞”的老陈、老杨、江月,还有很能暴走的大灰狼。据说从这里下入深沟,有一条河,沿着河走十五里到水泉,老王已经下去了,可大灰狼说一直没有找到那条河,为保险起见最后决定依然走公路。大灰狼下去找老王,其他人先后出发走到一处地势高且显眼的地方等候。大灰狼从沟里爬上来,又走了冤枉路。老王回来说,刚才大灰狼若再晚一步,他在沟底转过弯去,就听不见人喊他了。那沟里阴森恐怖,风吹来阴凉阴凉的,他一边走一边起鸡皮疙瘩。要真来条大灰狼,他可毫无抵抗能力。 Go,go,go,好累好累好累,在前队可以比后队休息得更多。我们过边墙,穿农田,走公路,一路走一路拍照。跟着大灰狼难免多跑路,好汉很得意地叫我记他捡了块陨石,我却不以为然。我们边走边问路,再用对讲机和后队联系。这里人说的里程没谱,在立有“扶贫攻坚纪念碑”的许家湾,我们对离水泉还有多远就得到两种说法,一是五里,一是一、二里,而当我们从这里下山,走过干涸的河床,登上公路,真正到达水泉的时候,发现离许家湾至多不过三里的路程,那第二种说法比较可靠。 这里的房屋分布在柏油公路两侧,地图上显示,长城大致从东南而来,在山下被公路截断,又上山向西北而去。以长城为界,北为内蒙清水河县,南为山西偏关县。大灰狼、好汉和老王坐在河床边砖窑上等着后队,我和老陈、老杨、江月进了路边一家旅店休息。这旅店一排五间砖房,都盖成窑洞式样。老陈问店家有没有养鸡,我对店家说要是养了可得藏好。几天没好好洗洗了,这下要讲讲卫生。店家打来清水,我们轮流洗了脸,又用热水舒舒服服地烫脚。老陈烫得高兴,扯开嗓子又说又唱好不痛快。 大队人马陆续到来,安分、2386、累了、歇了等几个腐败分子已经在晋蒙交界的地方喝过啤酒,晓月自称是一路认着老王的大脚印而来,不停说早上看了大灰狼一眼,再见就是晚上。石头和亦尘最后出现,他俩一路拍片,一路说着相声,你一言我一语地互相吹捧着慢腾腾地过来,分不清逗哏和捧哏,被称为一对儿“话腻子”。火箭接受老陈的提议,决定就宿此店。 晚餐有土豆丝、烂腌菜、大烩菜、摊鸡蛋、米饭和面条,菜做得很咸,火箭等出去买了啤酒。小方早就在念叨,她每进一村,不看房子不看瓦,就看哪家的鸡肥。饭后围坐大炕,拿出资料商讨次日的行程,和店家商定,明早要车来接。 水泉之夜,是山西六日最腐败的一晚。 山西长城六日记之四:偏关和老牛湾 偏关县地处晋陕蒙三省、区交界处,偏关为外三关之一。早起收拾停当,我们便驱车奔向西南方向的偏关县城。老王说,晚上我的呼噜最温柔,并且有头有尾,能起催眠的作用。好汉的“陨石”已经被他扔掉了,不停根据今天的去留情况重新分配食品,歇了很不平衡:回去背的比来的时候还多,够半年活动用的了。 一个多小时后到达县城,终于得以面对这北疆之门户,京师之屏障了。史料记载,这里东衔管涔山,西近黄河,北连内蒙,南通雁宁,自古为兵家征战、驻防之地。劫后余生的南城门保存完整,当地政府在去年根据资料重修了门楼,门洞上方的金字匾额“偏头关”是胡富国的手笔。城门东西两侧,分别建有一座白色马赛克贴面的现代建筑,内有银行、旅店等单位,和古老的城关紧邻而居,显得不伦不类。我们十八个人一下车就开始引人注目,不停提议,因偏头关东仰西伏如人首之偏,合影时大家也都要把头歪向西边,我可不想让人看了照片觉得我落枕。 由南门入城,见城内是一条南北向的大街,宽不过十米。两旁店铺林立,街上人来车往,十分热闹。城中还存有一些古旧的建筑,财神阁坐西朝东,匾题“北盈”二字,财神么,自然要营利。大街的北端是钟鼓楼,比南城门残破得多,上面是偏关县博物馆和文保所,工作人员说曾在建国初期修缮过。按说钟鼓楼应当建在街道中心,且史料记载偏关县城仅存南门,可偏关钟鼓楼建在街道尽头,又非北城门(从钟鼓楼出去,已不见城墙),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游过县城,再乘车去桦林堡,老陈、老杨和江月留下,将换车去忻州。中巴车在公路上行驶,沿途所见,有矿区、铁厂,工业污染严重。 四十分钟到达桦林堡,首先拍下清楚的石刻匾额,然后由马道登城观望,最喜观音阁内的一纸横幅“好人平安歹人愁”。桦林堡靠近黄河,这里的边墙为偏关县辖长城最好的地方。村中有城隍庙、老爷庙和龙王庙,均已废弃,但保存有大量完整精美的瓦当和砖雕。穿街过巷,我暗自替老陈可惜,因为这村里有鸡,小方的眼睛怕是不够使了。2386给村里的娃子们拍照,结果成了孩子王,一二十个娃子围着他到处跑。 离了桦林堡,原路返回,在接近偏关县城的地方转弯,走河尧线。再一次目睹偏关工业污染的严重,山谷中一条小河正流淌着黑色的水。途经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工程,见这里已经形成一个大镇,河谷中一座孤峰上还有古堡残存。环道上山,许多地方还是碎石路,下临深谷,令人心惊。峰回路转,远处峡谷中出现一条大河,水绿波平,当明白那就是黄河的时候,一车人齐声惊呼。 老牛湾到了。这里东面是山,北、西、南三面是黄河,河面最宽处不过百米。对岸悬崖高耸,那是内蒙的地界。因万家寨工程将黄河截断,河水流速减慢,泥沙沉淀下去,使得原本浑黄的河水变成青绿。老牛湾的景致,倒有些象北京的龙庆峡,可这里有黄河,非龙庆峡可比。 老牛湾堡建在河边半岛高坡之上,周边土地已明显沙化。城堡形制保存基本完整,我们由瓮城入南门,见迎面是座石影壁,影壁后面,观音阁和关帝庙分列左右,面南背北。寺庙建筑残破,内中供有小型的观音和关公神像,墙上有壁画,案前有香火遗存。堡中还有一座“诸神庙”,残存有彩绘诸神,墙皮剥落,我不忍再用相机拍照。民居分布在古堡内外,堡外北侧平地上,有座保存非常完整的砖砌敌楼,即为老牛湾墩。脚下是几十米的悬崖,原本建在河边滩地上的边墙早已被黄河冲毁,只有这敌楼依然屹立于此,好似一名威武的戍边军人,忠于职守,无所畏惧。我们在古堡内外疯狂拍照,安分泳兴大发,穿着纸内裤和好汉一起下水,畅游了黄河。 分队的时刻终于到了,没有被江湖拖垮的小方率领着总共十人的队伍先行返回偏关,最迟要在六日早晨赶到北京,剩下火箭、不停、石头、亦尘和我留在老牛湾。原本热热闹闹的山西长城之旅仿佛一下就归于寂静,感觉多少有些凄凉,好在还有两个话腻子不时地插科打诨。 晚上我们在东山坡上扎营,火箭等去附近农家打足了用水。夜幕降临后,只见对岸的内蒙人家灯火一片,可老牛湾堡就只有两三家点灯。火箭说,老营那里也是有人有电舍不得用。这令我不禁想起,曾经在山道两侧看见过“同网同价是民心工程”、“网改是德政工程”的标语。 夜空中,北斗星为我们指示着方向。据说,在当年辽人的心目中,那七颗星中的第六颗,就是杨六郎。 山西长城六日记之五:故寺 太阳出来我爬山坡。老牛湾这一夜,到底没能见到江湖从对岸偷渡过来。地席上扎满了刺,拔营后登山的路上,石头纵情高歌:“你晓得,天下黄河几十几道弯咧…” 这次我是前队,对讲机的电池富裕,闷了可以聊天。长城断断续续,在山谷中向东延伸。翻山过沟,两个腻子为抄近道曾下入深谷。路上看见了一条小蛇,中途休息的山坡上,山风有四五级。有的路段越走越象是在北京,令我很感不快,在这里我更喜欢黄土高坡。 中午时分到达滑石堡。史载该堡建于明宣德年间,北临长城,东接水泉,西望河套,内屏偏关,外近大漠,是偏关的极边要塞。存留至今的南城门上,有石刻匾额,上书“镇宁”二字。细观落款,是一大群文武钦差委宣滑石堡几个地方官所刻。见此,我真替这些地方官难过,他们头上有那么多的婆婆。南门楼上,有石碑一通,为明万历十年所立的《创建滑石堡砖城记》,碑体完好,字迹清晰,是滑石堡守备常世爵所立。从碑文中可以了解滑石堡的规模形制,得知修建这座城堡是为了防备胡人,使其知道明王朝边防严密,不敢轻举妄动。这是此行所见唯一一块详细描述所在城堡的石碑,非常难得,火箭不辞辛苦,从头到尾耐心地把碑文抄录下来。我觉得可以成立小站考古队,亦尘说要以火箭为首。 在滑石堡内外转上一圈,发现它的规模虽不及老牛湾,保存的完整程度却也不在其下。城墙的外包砖厚度超过一米,足见当年修建得有多么坚固。城堡西南面有一黄土墩台,长城从城北平行延伸过去,又转而向东南上山。两个腻子在城中采风,又和不停把娃儿们排好了照相,就象校外辅导员。深山古堡,平时难得有外人到访,村人都对我们投以异样的目光。孩子们敢于凑近前来,成年的大姑娘小媳妇则躲在门洞里,远远地朝我们这边张望,不时交头接耳,小声嘀咕着什么。 在村东头的小树林里,伴着随风飘落的沙土吃过简单的午餐,我们继续前进。用水又紧张了,下一个目的地正泥墕离此十五、六里,还不知道能否补水。记忆中,此后我们就是在一路狂走,四周都是黄土山,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走出去。一次次地问路,努力从听得半懂不懂的山西方言中寻找有用的信息。为走到对面山坡上的墩台,先要极不情愿地下至幽深的谷底,再上一个陡坡,穿过收割过的农田。土地松软,踩上去就象又到了敦煌鸣沙山。我走在最前面,火箭跟上来,放下背包又下去接应不停。两个腻子还在谷底不紧不慢地拍照,有时通过对讲机要我暂时消失,以免挡他们的镜头。日渐西沉,秋风萧瑟,昔日镇守在这里的将士该有多少次抚摩着边墙,想念他们的乡亲呢。 三个多小时后,我第一个进入正泥墕。这是个与长城紧邻的小山村,我进村不久就陷入了娃儿们的包围圈。打听得这里也只有坑存的雨水,为找辆三蹦子,娃儿们在我前后东跑西颠。村民说,离此四、五公里有个叫故寺的地方,早晨五到七点之间有去偏关的班车,不等人,上完了就走。五个人到齐后一商量,决定今晚到故寺宿营。走了一天,很疲劳了,还要接着再走十里左右,我的精神几乎要崩溃了,不由想起了安分形容小方的话:“同志们累了吧,再走五十里”!!! 好在这十里走的都是公路,还有幸在路边人家得到一点开水。中途停下来吃些压缩饼干,然后又是一声不响地狂奔。天在我们行走当中黑将下来,月光如水,用肉眼也可以看清道路,打手电只是为了告诉前后的同伴自己在什么位置。从来没有这样走过夜路,值得庆幸的是自己此时并非独行。道路曲折,路边不时还有至少一人多高的庄稼地,黑暗中谁知道那里有没有一双不怀好意的眼睛在盯着我们。我并不害怕,可右手仍在裤兜里紧紧地攥着瑞士军刀。这个时候,如果有辆三蹦子路过,如果我们拦在道上想要人家拉我们一程的话,那司机保证会吓得跳车逃命。 又是我第一个进村,到村口一个亮着灯的人家打听得此处确是故寺。这是个三口之家,小两口带个孩子。男主人姓郝,喊他的婆姨为我们补足了用水。郝家和刚才我们补过开水的那家一样,都是这一带的富户,用的都是开车到水泉拉来的自来水。 火箭在公路旁选定了营地。明天要回城了,今晚应该尽可能多地消灭剩下的食物。可帐篷外冷得呆不住人,没有时间多享受,吃过方便面就匆匆钻进睡袋。当地的口音,把“故寺”念成“故事”,石头感叹:没想到最后一天宿营,是个“故事”。 山西长城六日记之六:由大同回北京 第二天天不亮就爬将起来,顶着寒风等了一个多小时,顺利地坐上班车。火箭和不停在等车时嘻嘻哈哈地对练,我要他们来真的。这时候,先回去的两批人都早已平安到京。 回到偏关,在南门外小摊上吃过早点,然后乘班车再到朔州。拍下人家屋脊上的兽头,在朔州人的注目当中走过大街。找饭馆吃一碗面条,然后坐上中巴。汽车磨磨蹭蹭地上路,中途我看了一眼传说中杨家将血战过的金沙滩。到大同,买好回程车票,发觉车站建设比春节时又有进步。在大墙后街找了家饭馆饱餐山西风味,吃得松了裤带,肚子溜圆。饭后到附近网吧上网,在OICQ里见到河南快旅的好好奇和纤纤。不停等买了凉粉和老陈醋,我发现原来大同五龙壁就离此不远,春节时我曾路过此地,遍寻网吧而不见。回车站给家里打了长途,告知将于明早到京。“十一”期间车票紧张,我们五张票只有两个座位。不停把一个坐票给了我,他们四个干脆连那个座也不坐,铺开地席和防潮垫,在车厢衔接处的过道里唧唧歪歪地睡了一晚。我手中笔记不断,结果引起了乘务人员的注意,先后两次查我的票,问我是不是报社的,有没有任务,我当然都不是。不知是否他们内部打了招呼,总之后来当我问卖东西的乘务员站名的时候,他竟说不知道,样子很警惕。我不甘心,又去问车长,为了让他放心,还把笔记本拿给他看,车长的态度好得让我不好意思。买来的老陈醋瓶盖不够紧,流出了一点儿醋,搞得车厢里醋香四溢。 终于回到了北京,洗干净身上的泥垢,一夜过去,又来到班上,打开电脑,重新开始了日复一日的单调生活。 山西六日已成过去,告别了黄土高原和山坡上连绵不绝的边墙。我可以痛痛快快地喝水,再也不必担心用水不足。出门时我可以任意选乘车辆,再也不必为赶早晨的班车而狂走夜路。可生活在那大山里的人们,依然在用着发了臭的坑存雨水,依然在那崎岖不平的山路上奔波。娃儿们的脸似乎永远也洗不干净,一张彩色照片对他们来说也许就是奢侈的享受。在正泥墕,娃儿们为我跑前跑后,我不知该如何感谢他们。本想送他们苹果,可当时我兜里只有一个苹果,那么多娃儿,我给谁不给谁呢。 曾经感叹,古人用黄土筑就了长城,后来有的长城塌了,就还是一堆黄土。有谁晓得,脚下的黄土,曾经是长城? 黄土若有灵,只有她自己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