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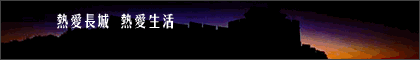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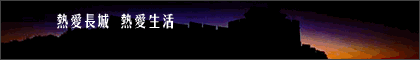 |
|
| |
|
13 2000年8月28日发表于长城论坛 夜里一点到达河北小五台山脚下的村子,在一个河岸露营。 共有二十二个人,我们长城小站十二个以及北京过客酒吧“先行野外公社”的十人。“先行”的朋友们似乎是成双成对的,在西直门长途汽车站集结时一看,有好几个MM。 清晨六点开始登山。这次我是参加一队,登上北台,然后在日落前到东台扎营。这是我参加小站活动以来强度最大的一次,心理压力很大。我是否能活着回来呢?或者说我是否能活着到达东台!有一点是确信不疑的,那就是我一定会被折磨得死去活来。这就是我的心理压力。 在山道上,有一次歇息时,我卸下包,坐着闲看。看到四只草叶形状整齐地并排生长着。我不禁想,它们这样生长有什么意义?它们周围满是草叶、草花和树,并不缺乏。这漫山遍野都是数不尽的草,就是有意义,又怎么会落到它们头上呢?那它们生长的意义何在呢? 突然我想到《道德经》里的一段文字:“天地之所以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这四只草叶并不是自己要生长的,非自生,而是天地要它们生长。天地其实也不是自己要存在的。天地和草都没有主体意识,因为它们不知痛苦地无知无觉,所以它们无所谓死亡。——老子说它们长生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人,我们是自己要出生、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吗?我们两只眼睛一个鼻子,是我们翻找图样自己挑中的吗?我们见到异性心中忧乐、我们有收获时心里尝了蜜似的,都是自己愿意的吗?——这些都是上帝给安排的。嫉妒、竞争、或者还有怜悯,这些都不是我们自己有意识的决定。 我们就跟这四只草叶一样,被出生、不得不生,并没被安排后面的意义和结局。所谓的生命,其实是一个谎言;喜怒哀乐,都只是在滥情。生命并不是自己的,不知道是谁的。佛家所说的三千世界,也没有真正的生命,这个世界其实是无生。我想是不是把它叫做无生界比较好。 禅宗里面有“无生”这个词,但手头无书,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意思了。(其实有也未必知道,因为那是个公案,没有经文的解释。) 在山道上,道边往往有一种蓝花,间或有颜色极深的。那道边极深的幽蓝,你停下来,仿佛会烧灼你的眼睛。 我自告奋勇地收队,落在了最后。后来我把收队的担子交给了卢沟晓月(我们叫他老妖),开始往前赶。渐渐地,早晨金黄、透明的阳光开始照耀头顶的树丛和山岭,给疲惫的我制造一种喜悦的氛围。我开始对着一座山头冲刺,山顶笼罩在阳光和它散射着的辉煌雾气之中。这好象是一座神山,我穿过一对对世俗欢乐的男女,盘山的小路总也爬不完,我就象虔诚的旅人为朝拜而付出着巨大的代价。 最后我终于疲惫地倒在一座山梁上面,——第二个休息地到了。除了小辫和冰水,我超过了“先行”所有的人。(这句话只是为“穿过世俗欢乐的男女”做解,没有其它任何的意思。) 再往后就是巨大的山脊和草甸,是一个适合用广角去描绘的世界。 中午两点我到了北台底下,离它只有一百米。因为在第二个休息地太长的等候,我们已比计划落后了一个小时。ANSEL上了北台,我们原地休息。 我被小范叫醒。那时一队其它的人已经走出一公里了。 后面的路主要是在相同的海拔上穿越,我似乎不觉得累了。 北台到东台之间有很多断崖,山脊就好象一个巨大的梳子,我们在找得到明确道路的时候,已经绕过了好几个齿,最后我们在一个小山口上发现找不到路了。 山上已经很难找到哪怕小块的平地,坐着都得小心不滚下去。 我害怕体力不够,不敢去探路,只是坐着观察。我觉得山脊上可能有一条路,我叫大道去走走看。大道慢慢消失在远处陡峭的山脊上。后来小范也去了。 最后大家决定反正就这样了。我也上了山脊,发现这的确是一条路。我追上小范,在一个一米宽的山脊上,听见前面的小范说了一句:“我们这样是在玩命。”的确如此,我另找出路,发现路在山脊左边的五米下面。 我看到小范时,他在一个比我高四五米的一个山脊的尖上,那里只够他蹲下来,前无去路,另一边是几百米的陡坡。我爬上去接他的包。这可怕的家伙竟然要在那么危险的地方把包卸下来拿一块巧克力吃先!我心惊胆战地看着他吃完。 ANSEL和吾睡找到了一条比我走的路低五六十米的路,那条路据说非常好走,他们在前面等了我们一个小时。 大道丢了他的包,包滚下了山那边的陡坡,他找了很久,他的包是绿色的。 天黑了,我们以为也快到东台了。最后精疲力竭的我们在暝暝暮色中满怀希望地登上一个山顶,绝望地看到,距东台我们至少还有两个较大的断崖,而且这些断崖我们都过不去。这时我们已经看不清地面,而且谁也不知道路。 前面的人已经下山绕道去了。坡非常之陡,而且滑。我自信没有生命危险,但我担心我后面的小范和卢沟晓月,以及在下面探路的人。这时候如果我们有一个人受伤,我们就全完了! 我们在陡坡上下滑的时候,吾睡的小摄影包也一下没看住,滚了下去,没影了。 我们必须得迅速找到营地,风很大,而且非常冷。大道丢了包,他和小拖还穿着短裤。我们先是准备在沟里宿营,后来发现沟里坡度太大。我们决定豁出去冲上眼前这道坡,如果翻过这道坡还是一条深沟、找不到平坡宿营的话,我们就惨透了! 我第一个冲了上去,大道背了小拖的包,他们来过东台,小拖第二个冲了上去。 我说不清这道坡有多长。有过登山经验的人都知道,你看得到的坡顶,等你到了那里之后还会看到一个坡顶,如此循环。 我不知道自己哪来的体力,我早就发现你不停下来,让肌体适应了那种极限的疲劳之后你会走得更远一点。这时我也这样。我有时让自己双手揪住草、跪着歇息三到四秒。这时我偶尔有空望望天空,我吃惊为什么我两手都是湿漉漉的而天空却是漫天星斗!这古怪的小五台!我更多的时候站起来走,而不是在爬,我终于上了顶,第二名在我一百米以外。我初步找到了营地,知道我们可以没事了。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后面的人,因为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的拼命,如果万一告诉了他们坡顶有营地,他们会不会就在山腰上垮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犹豫一次,我终于没有做声,我走到坡顶的另一边,看看有没有更好的营地,最后卸下包躺在湿漉漉的草窝里看星星。 然后就是我钦佩别人的时间了。我没有帐篷,也不太会搭。他们在冷风中支帐篷、做饭,我觉得体力好的、体力不好的,这时都比我更能忍耐痛苦、更能在痛苦中勤劳。吾睡给呆在帐篷里的我端来一碗热方便面后,我有了出去吃东西的兴趣。第二天早晨的阳光快乐地照醒了我,美好的一天来到了! 我们在草地上煮早餐,山顶上没有厕所,有人跑远一点去“练功”(他们都说是在练XX功:-)空气清新无比,山那边煮着一锅几百平方公里的牛奶,阳光下山坡上有着各种颜色的草和花。我翻找我的水,发现包里至少不见了两瓶水,一瓶是我的,一瓶是我代绿野的冰水背的,他有着我们这里最重的包,是个好样的!我叫了一声,吾睡告诉我我的水在小范那儿。我明白了,我在北台下睡着的时候,他拿走了我包里的水。 吾睡和ANSEL找到了相机,竟然完好无损。我对他从动物园门口摊子上买来的摄影腰包钦佩不已。我们下山,穿行一条溪边小路,小路穿过溪中间的小洲时,两耳的溪水声爽极了!这条路我们走了六个小时,终于在乌云弥布大地的下午,走到了高粱和向日葵地的旁边,胜利回来了。 总计,大道丢了他的包,里面有红酒等吃的和他的相机;小范的包滚落山崖一次,只滚了三十米吧,胜利找回;吾睡的摄影包失而复得;我新买的野营刀掉落水中,送给山神吧:) 深夜一点我回来,发现美能达的DYNAX7发表了。一部震撼性的新机器! 中午我翻论坛,钦佩大道送给山神厚礼的豪爽,以及小范的柔肠善感。哈哈,又有两个“鸳鸯蝴蝶”暴露了真面目,一个是ANSEL,一个是小范! :-) |